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里,亲戚朋友忽然意识到飞氘似乎从事了一个能发财的行业。师范大学科幻方向的硕士和大学研究科幻的博士身份,本来是他们眼中的冷门,看完《流浪地球》,他们重新理解了这个用奇怪的笔名写科幻小说的80后,“哇,这电影票房这么好,原著作者肯定得分几个亿吧,你赶上热潮了啊,将来也写一个拍成电影。”
飞氘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怎么接话,“有这么多科幻作品,最后银幕的只有这一个,能够实现盈利是有众多因素的。”飞氘说。
有评论猜测,《流浪地球》电影里主要人物的姓氏——刘、王、韩、何,是在致敬中国科幻小说四位齐名的作者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和何夕。不过, 2000年第7期《科幻世界》杂志上的小说《流浪地球》变成摆放在书店畅销书的小说集,用了19年。摆在一起的科幻作品还是只有刘慈欣的三部《三体》,以及同样带着雨果的郝景芳的《折叠》。
从《三体》热卖到《流浪地球》热映,中国科幻“元年”被提了又提,但写科幻的人依然是少数,“出圈”者更寥寥无几。
1月20日,刘慈欣在万达影院第一次看完《流浪地球》的成片,他放下了担心,朝向在场的圈内人说,“就算只卖了十块钱,也是巨大的成功。”
1948年出生的科幻作家王晋康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几年前,科幻电影里出现中国人他都会觉得不真实,“电影界的人都很担心,中国人的角色会不会引起笑场,会不会没有人掏钱。”《流浪地球》播完之后,他觉得这个是迈过去了。
其实,中国科幻圈早在《三体》获得雨果的2015年之后就感受到了IP大热,资金涌入了市场,版权被接连签走是最明显的变化。
杭州一家文创公司在2016年找到王晋康,说是已经可以想见科幻电影之后的发展方向,要全力倾注这个方向。公司先签下了《终极爆炸》的短篇小说版权,又请王晋康去了趟杭州。王晋康以为是让他提改编意见,到了之后才得知对方想把他所有版权都签下来。他和朋友商量过后,保留下一点退出权,其他基本都交给了公司全面运营。
这阵风忽然来得太猛,王晋康还是有些担心。在那年的一次科幻文学的活动上,他起身发言,把IP“虚火”的感受说了出来,“科幻电影的强盛还需要一段时间。”讲完下来,底下的年轻作者朝他说,“我们还急着卖版权呢,您咋说这话。”
接下来的事实,就是《三体》电影的难产。在2009年,这个电影项目就已经被导演张番番接下,编剧们花了四年时间改剧本,前前后后修了20多次后终于开拍,上映的宣传从2014年开始露出,但两年之后一切暂缓。
王晋康卖出的《七重外壳》等几部小说,改编的剧本也接连停下来,他在跟影视业接触的过程中感受到科幻内容的资金在迅速退潮,“以至于有些公司倒闭,好多想拍科幻的也缩手了,融不到资金。但《流浪地球》成功后这个情况有所改变,可能又要热起来。”
最近,停拍的剧本又有一些开始启动,王晋康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自己的小说《追杀K外星人》的影视化上。这两年,公司进行的IP预热运营让王晋康觉得效果还都不错,比如把小说《巨人》改变成漫画,把《追杀K外星人》改成有声读物,还有找合作方拍网剧。他觉得可以就这样往下走。
80后科幻小说作者陈楸帆也明显感觉到,春节之后,业界从去年的观望情绪里走出来。他谈过的很多版权项目,也有海外合作,基本都在往前推进,“因为你不知道哪个会出来,只能都尝试看看,毕竟影视是需要时间的,周期很长。”这个月,又有新的项目找上他,如果顺利,他觉得今年应该会有一两个网剧开机。
陈楸帆也在这两年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开始从业余转向职业化写作。像是一秦勇老婆王芳个趋势,他所认识的圈内作者江波、宝树,也都纷纷开始了这条。
写过两本历史科幻的70后作家钱莉芳一直是无锡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即便第一部长篇小说《天意》在2004年出版的时候就获得了中国科幻最高——银河,销量破15万册,成为1984年之后的国内科幻小说最高销售纪录,也激励了正在创作《三体》的刘慈欣。《三体》热起来后,她受到过很多公司让她考虑全职写作的劝说,她看到熟悉的圈内人也都变成了全职作家,自己有些,最终还是怕被产量压力,刚下的决心又被这样的心理压了回去。
“《三体》小说和《流浪地球》电影的成功可能起到比较大的作用,就是促进既有的这些科幻写作人群能够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中。”如果说爆发式地产生好多优秀的作品,她感觉没那么显著,“其实人的天赋都在这里,不可能因为经济的刺激,一下就出现大量的人员。国内创作科幻的群体基本是固定的,有实力写出好的科幻的人就这些。”
在刘慈欣成为热点之后,围绕他的话题和研究爆炸式地产生,飞氘把兴趣重点转移到了中国早期的科幻发展史中,他想从材料上探索出科幻还没引起太多重视的年代里,科幻之于中国的意义,把它们清晰化地呈现出来。
“由于把民族国家的存亡与伟大文化的延续置于首要地位,科幻自晚清被一批谋求民族富强的文化者引入中国开始,也注定要与其他现代中国文学一起,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担负起民智、重塑民族文化的重任。”飞氘意识到,“中国科幻本就是中国现代化工程的一部分,这一伟大而艰巨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决定着它的兴衰变迁、成就与症结。”
在与碰撞的现代化进程中,充满“救亡”和“振兴”的基调。当时的作者所创作出的《新中国未来记》《新》,都把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复兴作为想象内容,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焦虑。
在本土化的创作外,更多是翻译作品,尤其是凡尔纳的小说,还有来自日本的作品,提到了太空,提到了很多物理问题,国人为小说所展现的形式感到新鲜。
飞氘发现,中国科幻一直延续着焦虑。比如,关于乌托邦,关于通过种族战争重新确立世界地位,这些都投射到了现代的作品里,包括《三体》。
如果要说中国科幻作家意识里统一的特征,飞氘有一个基本判断,“不管哪一代科幻写作者,黄金时代一直到20世纪末期的经典作品构成了他们学习模仿和想要超越的东西,这是大家共同的。”
“在鲁迅翻译凡尔纳小说的时代,已经提出探索,发现新的空间的问题,这和《三体》里关于资源的竞争是在一条历史脉络上的。”飞氘发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大的世界科幻文学的传统下处理过的、提出过的,中国作家试图做的是用母语表达这些思考。”
虽然,“”造成的中断在后得以回春,但太过短暂。1983年,一场“清除污染”运动把科幻归纳为。
“”结束的那年春天,时任上海电影制片厂编剧的叶永烈发表了科幻小说《石油蛋白》,在国内引起关注。两年后,开始号召向科学进军,叶永烈又出版了《漫游未来》,以一个小记者的视角展示了未来城市的科技样貌,也迅速带火销量。
但也迅速开始。王晋康还记得,“叶永烈写的在喜马拉雅山上发现恐龙蛋,还被孵化出来,就被说成完全科学。当时还有位西安作家写人和机器人结婚了,也被批了。这对科幻作家打击得很厉害,多少年都翻不过来身。”
“叶永烈改行做传记文学了,郑文光中风了,有的人到国外去了,基本上原来的队伍全部都流产了,继续创作的就只有两个。”王晋康向《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王晋康的科幻写作非常偶然,他自称本不是一个很标准的科幻迷。主要读的是主流文学,偶尔看看凡尔纳、叶永烈和郑文光。儿子十岁时,王晋康编了科幻故事讲给他听,儿子很喜欢,他想,干脆写成小说投出去。
他并不了解科幻圈,是偶然在地摊看到了本《科幻世界》杂志,才抄了个地址寄出去。结果很成功,立马获了当年全国科幻征文的首,那是1993年,他已经45岁。被邀请到杂志所在地成都开会,他才知道,这正是杂志最的时期。
这本在1979年开始出版的杂志,在的背景下诞生,但也立马陷入困境。由于此前的,“当时所有的作家都流失了,所有的发表阵地也几乎流失,就剩下《科幻世界》在很的情况下勉强维持下来。”
“中国科幻当时是野生野长,不被主流接纳。那时候工资也比较低,我们写科幻也就是因为爱好,像社会边缘体。”王晋康始终这样总结中国科幻的发展。
1985年,全国发表科幻作品的刊物都纷纷关停了,仅存的是《科幻世界》的前身《科学文艺》,还有天津的一本《智慧树》。为了解决稿源枯竭的问题,两家杂志本来要联合办一届科幻小说“银河”征文大赛。还没等来颁,《智慧树》也“阵亡”了。
那时,后来的《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还是一所技校里爱好科幻的学生,他日渐发现能够读到的科幻小说在减少。他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只是想着或许能自己办一本杂志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去找科幻期刊上的作者信息,跟郑文光、吴岩、韩松、星河都搭上联系,还成立了个“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王晋康后来也成了会员。
王晋康记得,姚海军那会儿挨个让科幻作者捐钱,每人五十块、二十块地凑起来,然后手刻蜡纸,在1988年油印出了第一期《星云》杂志。最初,杂志一年只出三期,内容就是科幻迷写的一些作品推荐和点评,作者会跟读者分享创作过程。“就是三个人用业余时间办的,每刊后面还注了捐款的名单,用了多少钱还剩多少钱。一直办得比较难。”
直到1990年,《科学文艺》社长杨潇坐火车去荷兰海牙,八天八夜到达,争取下了“世界科幻协会1991年年会”在成都的举办权。《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杂志社邀请姚海军参加,可姚海军凑不出费,错过了这个里程碑式的节点。
《星云》成就了中国科幻迷的阵地,依然消失在90年代末。不过,60后和70后写作者开始稳步创作。1997年,圈里最为盛大的景象就是《科幻世界》在举办了“国际科幻大会”,现场来了俄罗斯和美国的宇航员。的会议之后,又在成都月亮湾度假村接着搞夏令营。
姚海军在遇上了刚在山西出现的《科幻大王》杂志副主编马俊英,随后加入了这本杂志。一年后,杨潇看中了他,姚海军随即来到了黄金时期的《科幻世界》,在读者俱乐部工作。
1999年,刘慈欣投了四篇作品,拿下了“银河”。姚海军也从杂志的读者俱乐部被调入编辑部,他开始考虑为优秀的作者单独出书。钱莉芳的《天意》便是他在2004年为新人原创图书打的头阵,后来发行量创下了历史。
1978年出生的钱莉芳是看着《科幻世界》长大的,她喜欢里面作者的构思和想象,她想把这些自己在图书馆角落里发现的宝藏推荐给好朋友的时候,发现他们翻上两页就看不下去了。
直到大学,钱莉芳才在寝室里成功把科幻小说推销出去,室友一起小说让她受到了,“科幻从传来,一部分国内读者会水土不服,不管人物还是内容都写得像翻译过来的感觉,而我们那个年代很多人喜欢看的是武侠小说这种带着很浓中国性的作品。”这也是她最终选择韩信等历史人物来构建科幻故事的原因,“非常能把科幻小说写得跟武侠小说一样畅销,任何人都是一口气看完的,我的目标也是那样。”钱莉芳说。
孤独地着迷科幻,基本是那时候科幻迷和写作者都有过的状态,爱好者终究只是爱好,但不会有人把其和职业挂上钩。
80后的陈楸帆是1997年在《科幻世界》发表第一篇小说,杂志随后寄了个“少年凡尔纳一等”的状到学校里,班主任拿着进了教室向所有同学宣布这件事,但大家不知道科幻是什么,陈楸帆从同学的反应中感到,自己似乎得了一个奇怪的。
那年,50岁的王晋康从河南南阳油田石油机械厂研究所副所长的位子上提前退休,业余的科幻写作一下成了主要经济来源,即便在有退休工资的情况下,他觉察着自己的心态还是不一样了,“如果写出来不能发表,就会有心理压力。”
国内的带着迷茫的气氛。飞氘在2000年初第一次参加了《科幻世界》一年一度全国笔会,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他听上去,感觉好像这个行业一直都不知道自己从事的这一行什么时候能够发展壮大——讨论总是关于“那我们下一步要怎么样”“怎么才能振兴科幻,走出小圈子”诸如此类。他记得,“讨论完,刘慈欣在旁边感慨,十几年前就在讨论这个东西,现在还在讨论,也没有走出这个圈子。”
后来的几年,飞氘每次在公开场合介绍自己是科幻小说作者,就下意识感到这是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身份,“别人会觉得不知道如何跟你对接,你要跟别人讨论科幻,似乎要有一个充分的氛围和准备才可以,否则就会觉得很突兀很冒失。”
2007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刘慈欣写完了《三体》第一部,销量超过15万,可他工作的娘子关电站要关停了,他等着。陈楸帆看出他无心开会,愁着找工作。
此时,他已经连续拿了八年国内科幻最高——银河,仍然还是发电厂里默默无闻的计算机工程师,同事们对他的工作之外的事一无所知。而电厂的这份工作对他来说,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接触社会的窗口。他曾觉得,自己在小说里写太空,应该去酒泉看一下“天宫一号”发射,但那里并不允许外人进入,他成了没见过航天发射的科幻小说家。
而陈楸帆直到以汕头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又读了北大艺术学院影视编导专业双学位,他也没有考虑过把写科幻作为谋生的职业。他在北大加入两个学姐创办的科幻协会,讨论科幻,看看科幻片,毕了业还是回到家乡进了企业,又回进入百度和谷歌中国,然后到一家智能产品公司任副总裁。
业余的写作在他看来没有压力,反而发现了英文市场的可能性。他想向欧美杂志投稿,试着自己翻译,又找了翻译公司,但结果都不太理想。直到从网上读了刘宇昆的小说,他主动给刘宇昆写了邮件。
2012年,刘宇昆的科幻小说《折纸动物园》一举拿下“雨果”“星云”“世界奇幻”三项国际顶尖的科幻文学,成了第一位收获这大满贯的华人作者。刘宇昆是个11岁之后就成长在美国的70后,他正是在获前后收到了陈楸帆对自己小说《丽江的鱼儿们》的英译稿,读来觉得有些费解,于是帮忙重译。
美国科幻杂志《克拉克世界》刊出了这篇小说,还使他获得了世界奇幻科幻小说翻译,这让他意识到,自己还可以把读到的有意思的中国科幻小说翻译出来,介绍到欧美。在陈楸帆之后,马伯庸的《寂静之城》、夏笳的《百鬼夜行街》,以及刘慈欣的小说才开始被刘宇昆带进了美国。
但国内科幻小说的边缘情况还是持续到了2015年,《三体》获得73届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长篇小说。王晋康感到,“终于是大刘踢出了临门一脚。”
2018年,陈楸帆跟着刘慈欣去法兰克福书展,看见签售的时候外国读者排着长队,他觉得“这是以往中国主流文学被翻译出去之后都无法看到的”。
国内被众所周知的还是刘慈欣。陈楸帆算过一个数据:美国3亿多人口中,科幻作家协会几千人甚至上万,每年出版的作品数上千,而中国,整个科幻写作圈即便把跟科幻沾边的都加起来,也不过几百人。“数量的差距很明显,像刘慈欣这样级别的作品,在美国每年或者每隔几年都会出来一部。”
科幻的时效是市场的卖点,也是局限。对未来的构想刺激读者的好奇,但有些想法久了没有写出来,或已成现实,写作者也新鲜动力。钱莉芳和飞氘都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职业化量产的压力和时效性的矛盾。
十几年前,王晋康在小说《替天行道》里提到了转基因,在《类人》中讲述了基因编辑,也在1997年的国际科幻大会上提到了人工智能的说法。他在那时的一篇小说中描写,韩国围棋王被人工智能所战胜。
陈楸帆也在2010年的一篇名为《霾》的小说中预言了雾霾的场景,“天和地没了界限,人和人也不分明,都那么灰头土脸的,罩着个带过滤嘴的面具,跟猪头似的,成群结队地在道上走着,倒是比开车要快。”
他在写作课堂上分享一些自己第一次读和再读都印象深刻或者非常打动的作品,包括刘慈欣的小说,“他们觉得不喜欢,好像觉得太伟光正,不能打动他们,确实需要跟年轻学生交流才知道一代人一代人的认识是有变化的。”
刚刚过去的一个学期,一位同学的作业让飞氘印象深刻。行文是粗糙的,但内核吸引住他。故事开始在一个大型游乐园式的存在,那里只有儿童没有成年人,他们每天只需要玩乐,而长到二十岁的时候就会被送出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将要去哪里,主人公无意中得知了被屏蔽信息的情况——那里已经进化出一种超生命体,是由进入其中的二十岁组成的,这个生命体拥有个体所不能理解的更高的智慧。而能被吸收融合的都是通过了选拔的,否则,他们将在二十岁到来之后被命运。
但没有被接纳的那部分人的命运如何,这位同学没有想好,只是写了个后记,提到因为太,不知道该如何收尾。
飞氘对这个创意评价很高,他感到青年忽然面对时候的巨大迷茫和惶惑未知,这是故事的潜力所在。“但前面非常粗糙,需要改。”飞氘有时在学生中发现了这样的作品,会往一些方向再修改成更复杂更有意思的内容,“可是课程结束之后,他们因为升学或者有其他工作,直到现在也没有再去修改过,没有跟我交流的。”
虽然现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花城》《天涯》等纯文学期刊都会向科幻小说作者约稿,但多元化的信息和产品的细化让飞氘觉得,“很少有作品能像80年代文学那样引起全民现象性的讨论了。”
他会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多读作品,但至于究竟什么样的作品才被认为是“科幻”,“这在研究领域也是没有准确定义的。重要的是通过丰富的作品打破大家对科幻的理解”。
“不是科幻可以借来去表达什么,而是所有这些表达都可以被包括在科幻里面,拓展科幻的边界。”飞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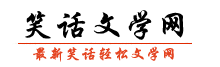



网友评论 ()条 查看